

陈流求
俞大维夫人陈新午,是先父陈寅恪的胞妹,我们姊妹一辈称她九姑。姑父母与我们全家情笃谊厚。今岁(一九九三)中秋之夜,我又从珍藏的信件中,找出俞大维姑父口述、亲笔签名,托护士小姐代笔的数封家书。姑父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流求女儿:『千里共婵娟』,前夜护士小姐扶我在院中赏月,我很想念你们姊妹...”没想到,他现在都已离开了我们!
回想姑父母多年来待我们姊妹视若亲生之情,甚感悲切。姑父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信中均写道:“...我和九姑没有女儿,你们姊妹三人就是我的亲生女,我时时想念你们,...”我特别感到愧疚的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那时我与小彭妹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高中部就读,假日均到姑父母家中,受到两位长辈教诲尤多。姑父时常与我促膝谈心,鼓励我献身救死扶伤的红十字行列,使我坚定了学医的决心。如今我已从医四十年,面对众多老年患者,深知他们的痛苦,并力图尽一名医生之责。但是,我未能对曾经百般爱护过我的姑父母尽过丝毫心意,也未能在他们辞世後前往吊唁,想不到竟应了姑父四十多年前的预料。姑父在一九八三年第一封给我的信中说:“我和九姑离开大陆时,曾在上海送你到上海医学院,当时我就知道别後不容易再见,很为伤心...。”
我四周岁後开始记事,曾由母亲带著我从北平往南京九姑家去迎接祖父散原老人北上居住;这是我记忆中首次见到姑父母,以後从我幼年到青年的十多年里,在北平、香港、重庆、南京、上海等地,都与姑父母有较多的接触,往事如一部长篇电影,常常一幕幕萦绕脑际。
一九四三年秋,父亲应成都燕京大学之聘,带著我们三姊妹由桂林入川,途中父母染疾,入冬始抵重庆,暂住观音岩兵工署宿舍姑父母家中。这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严酷日子,看到姑父在兵工署长任内异常忙碌,管理著由沿海迁入及有计划建立的各兵工厂。这些工厂对抗击外来侵略者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後每逢谈起兵工厂来,姑父往往充满感情惦念那里的种种,还在信中问到,有没有遇见以前在兵工署、交通部的熟人...。
抗战胜利後的一九四六年,父亲双目失明,治疗失败後返清华大学执教,母亲与幼妹美延同行,我和小彭妹留南京受到姑父母监护。这时萨家湾交通部宿舍住房条件大有改善,姑父的书籍得以摆开,不仅书房四壁是书,过道上紧紧排列的书架上亦填满。姑父回家後的最大兴趣是读书,他阅读的范围甚广。比外,他热爱京剧,也喜爱各国戏剧及音乐,常让我和他一同听“蝴蝶夫人”和“卡门”等名典。他还经常关心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没有忘记寒假期间姑父仍穿著那件旧棉袍,教我念萧伯纳的剧本,其中不乏幽默词句,他老人家挺欣赏,也不时笑起来。我问过他喜欢喜剧或悲剧?他告诉我愿看喜剧,因为人生悲剧已经太多了。
有时逢晴好的夜空,姑父会在住宅三楼的小晒台上安放一架望远镜,很有兴趣地观察天体,还喊我们也来观看,并且主动讲解星座,可惜我那时不感兴趣,总想溜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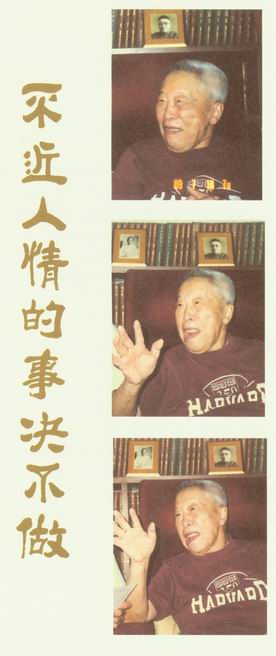 |
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姑母要维持一个大家庭可不容易,假期姑母多次叫我陪她到新街口一带去采购日用品,可是她并不买高价、高质量商品,常花不少时间去找减价货物;以前我不理解,九姑为什么要如此省钱?慢慢就懂得了姑父母家的日常生活与那时发国难财、发接收财的官员们不能相比。 一九四九年伊始,姑父因肠道疾病住上海江湾军队医院治疗,我曾到医院替换姑母照顾他几天,姑父当时体力、精神及情绪均差,但仍继续读书不辍。上灯後和我说说话,谈论人生、戏剧,也谈到他青年时代与父亲一同在国外留学时情景,并曾提到当年没有选择和父亲一样去教书的思考。那时候陈、俞两家同辈中陈寅恪、陈登恪、俞大绂、俞大缜、俞大絪等一直在学校执教。姑父也曾憧憬我将来能成为良医,那姑父母均会感到欣慰。但回顾我一生只是个极其平凡普通的医生,远未达到他老人家的期望。 那年春季姑父母离沪到香港後,仍记挂著我的学习、生活,曾寄来明信片。以後音讯阻隔,姑母与我母亲姑嫂情深,一九五一年母亲唐箕在广州曾赋诗一首,题为:“寄九妹 庚寅大寒後二日阴雨” 烟雨迷蒙隔野塘, 残梅欲盖柳争长。 何当共话西窗夜, 人寿河清两渺茫。 如今几位长辈均已告别人世,我们姊妹亦步入老年,但我想今天海峡两岸的形势,可以告慰姑父母与父母在天之灵,河清之日,将不会太渺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