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荔荔
我小时侯,家父跟我们谈天,有时会提到他师友或上司。我十五、六岁时就已发现,俞大维世伯是家父最崇拜的师友中的一位。每次家父谈到俞伯伯出奇的脑力;高尚的节操、人品;能做事,肯做事的精神;不屈不亢及爱护部属的态度;家父不是咋舌称奇就是脸上洋溢著由回忆引起的快乐。我听得津津有味,心想不知我是否有缘会结识这位长者。
一九五三年,我赴美求学第三年,得肠溃疡。九死一生,开刀两次,住院冶疗七个多月,因为没有健康保险,欠了医院一大笔债,家父母远在台湾,且公务人员没有积蓄,无法帮忙。我只得靠中、美友人接济。俞伯伯那时正在华府公干,经济情况也并不好。可是听到我的困难,慨然寄了一百美金给医院,助我度关。
次年我病愈回华府附近的威尔逊学院进修,家父嘱我到俞府上,向俞伯伯致谢。我托一位与俞府相熟的朋友带我引见,说明来意後,俞伯伯仔细看了我一眼,微笑著说,“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帮忙是应该的。”随即留我吃饭。那晚俞伯伯俞伯母请了约三十位客人吃自助餐。客人中有些是俞伯父、伯母一辈的长者,有些是年轻人。不过据我观察,似乎以我年纪最小。我拿了一盘菜肴坐到远远的一个角落,等待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来找我谈话(据我以往经验,在这种场合,多半是长者与长者谈话;上研究院的年轻人与别的上研究院的年轻人谈话;小萝卜头找小萝卜头谈话)。没想到俞伯伯拿了菜饭以後,竟坐到我旁边,问我在大学里主修什么。我说:“主修英文文学,副修法文。”他很高兴,又问我看谁的作品,我说了几个二十世纪英国作家的名字一Virginia Woolf, E.M.ForSter, D.H.Lawrence一满以为身为数学家、兵器学家的俞伯伯,对这些作者不会感兴趣,没有想到俞伯伯不但看过他们的作品,还对这些作者有独特的见解。
 |
一九六二年,我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到京都、台北、伦敦、巴黎做研究及环游世界收集资料,在京都时得家父信,告我俞伯伯、伯母已返台北;嘱见我带一份礼物回台送给俞伯母。我选了一块纯丝我认为俞伯母会喜欢的衣料。回台後数日,谈话间,家父提到散原老人及陈寅恪先生是俞伯母的父、兄,也是俞伯伯的至亲好友。我在美时,读过散原老人诗集,看过寅恪先生的文章,对他们非常佩服,我惊喜之余,脱口而出,“咱们今天就去拜访俞伯伯、俞伯母。”当晚驱车至俞府。俞伯伯、俞伯母外出。随後又去了两三次,他们也都不在家,一周後我离台。那次回台竟没有见到俞伯伯。 |
一九七六年,家父退休後十年,因气喘,肺气肿,身体衰弱不堪。家母也患了老年脑衰症 (Ajszheimer's disease)。家姊跟我决定,再接家父母来美,跟我们一块儿住。我那时已开始在波士顿塔福茨大学任教。向校方请假一年,又得到美国学术会总干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资助,预备先到台北接父母至美国,再由美国返台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写书。离美前我寄了一批工具书到台北,准备写作时用。
一九七七年一月初,送家父母至美返台,打开由美国寄台的那包书,预备开始写作,一开包,见一便条,通知我包中有三本书一中原音韵研究,从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和说唱文学史一被没收。我颇惊讶。因此三册虽是大陆出版,可是是纯学术性质,毫无政治色彩。我又著急这三本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书已成绝版,再也购买不到,给某单位打了十几次电话,问不出头绪,急中生智,想到前任国防部长的俞伯伯可能肯托他某单位的熟人帮我查查看书的下落。到俞府,正好那天有侍从罗上校值班,俞伯伯听了我的陈述,跟罗上校说:“纯学术的书,不必没收。大概那位职员无暇查阅,弄错了,请你去替陈教授问问。”(後来此三本书,某单位找出,寄回我美国住宅。)
当天俞伯伯留我吃饭,饭後看戏,他说:“不会有好菜给你吃,不过你甚么苦都吃过,吃坏了一顿舨,算不了甚么。”开饭後,俞伯母坐轮椅由护士推入饭厅。廿多年不见,俞伯母完全变了一个人。俞伯伯指著我跟她说,“这是陈树人先生的四小姐。”我趋前鞠躬。俞伯母看著我,见面不识。口中喃喃,不成言语。我含泪走到座位,看见桌上只有一荤、一素、一汤、一饭。乍然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驻重庆新闻记者Theodorc White在中国写出雷霆(Thundes out of china) 一书,极力批评政府官员,只有三位得到他的推崇,一位就是俞伯伯,被White赞扬为“廉、俭”。又想起另一传闻,说俞伯伯如何与士兵共甘苦,士兵吃甚么,他也吃甚么,士兵营中没有火,他屋中也不生火。俞伯伯很快就吃完饭,不过仍留在席上,频频把菜夹到俞伯母盘中,由护士喂俞伯母吃。我们虽不停的谈话,可是我感觉到俞伯伯分秒都在留意俞伯母的动静。饭中他说了一句话,使我耸耳注意。他说他在欧美时,也常看莎士比亚话剧演出,可是他觉得国剧比莎剧更有意思,我问他为何,他说:“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能是因为我开始看国剧是在快乐的童年。现在一听见锣鼓声,只觉得兴奋快活,就是天大的忧虑,也忘得一乾二净。到剧场,几位服务小姐围过来,亲切的称呼”俞公公“,搀俞伯伯入座。锣鼓声一起,台幕一升,我转头,果见俞伯伯面带笑容,聚精会神,目中炯炯有光。剧中幽默处,俞伯伯鼓掌哈哈大笑,完全一副小孩过新年的姿态。
一九七七年四月上旬,我由台北到纽约领美国国家著作奖前,去问俞伯伯有没有甚么东西要我由美国带回。俞伯伯听说我获奖,很高兴。说东西是不需要,不过希望我回台北後在台大文史研究院给他的学生及别的听众演讲一次。我惊讶地问:“我不知道您在教书,多久啦?”他说: “有一批台大研究院学生,每周到我家来一、两次,跟我讨论”。我问:“甚么题材?”俞伯伯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由东周、战国、文史哲学一直讲到近代。”我心中开了一朵花,好不快乐。伯乐找千里马,天下特号惬意事之一。
八月中,我返美教书前,选了一个雨後比较凉快的下午,去向俞伯伯辞行。在玄关听见俞伯母房中,传出护士教俞伯母说话的声音:“一”、“一”;“二”、“二”;“三”、“三” ;“四”、“...” ;“四”、“...”。上了客厅,看见俞伯伯一个人坐在走廊堆满中外书报放大镜的茶几前,身穿白中显黄的短袖衬衫,眼看窗外花草,脸上一副疲乏无聊神态。我一阵难过,心想俞伯伯好不孤寂凄凉。我得说点什么博他一笑。我那天正好看完美国杰出女作家Ann Beattie 的 Chil1y Scenes of Winter,脑中不停在想她书中那些六十年代,二、三十岁,对美国传统价值不满而自己又未找到方向的男女角色。脑中想甚么,口中说甚么,无暇深思,已开始向俞伯伯介绍这位新作家及她的作品,两三句话以後,俞伯伯开始问问题,不到十分钟,俞伯伯已面带笑容起劲地跟我讨论六七十年代美国新作家及年轻人的形形色色。兴高彩烈,大反我刚才看到的疲乏无聊。我心里笑我自己,刚才竟误认俞伯伯孤寂凄凉。喜欢看书思考,又精通数国文字的人,前後,古今、中外,学者作者都是他的兄弟姊妹;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他的伴侣。暂时的疲乏是不免的,长期的孤寂凄凉却不可能。我刚才的难过是杞人忧天,大可不必。
我起立跟俞伯伯握手告辞,请他保重,他拍拍我的肩膀,嘱我多运动,多写作。我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住又走回,说了一句“多保重,祝健康,再见。”走笔至此,欣逢今岁哲人悬壶之庆,天涯晚辈谨掬天锡纯嘏南山之寿为颂为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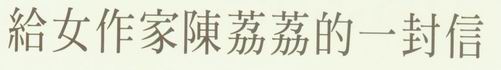
荔荔小友:
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我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阅人已多,发现文学天才难得一遇。但你却有文学天才,应该继续写作。写作须考虑叶落归根一写中国题目。我尚未看过一位中国文学作家写外国题目,而能长久获得成功。
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
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那能都看完了。
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恼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
我平生得益的只有一部半书。半部论语教我处世做人的道理。一部几何原理给我敏锐的逻辑思考和高度的判断能力。
问你父亲及家人安好! 祝
你平安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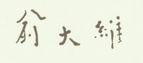
七十三年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