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追随 蒋公数十寒暑,其间经过多少往事,令人永远不能忘怀,愈追忆思 念愈多,尤其在 蒋公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在我内心深处深深的感激 蒋 公的知遇之感。 谨以在追随 蒋公时亲身所感受到 蒋公高超的人格和风范的几则小故 事,表达心中虔敬的追思。 当徐蚌会战最胶著的时候,我突接 蒋公来电话查询投粮的经过和结果: |
蒋公问:“今日投粮,有没有投到?”我答:“投到了。”蒋公又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又怎么知道这样清楚?”我报告 蒋公:“是我亲自坐空军运输机去空投的。”
蒋公对於我亲自把援粮空投到徐蚌战场一事,显然深感意外,也深觉宽慰。
那天投粮的经过,我记忆犹新。
飞临徐蚌战场上,仅见一片冰天雪地。想到地面我军将士在冰雪封冻中待援急切,我们唯有克服万难,达成投粮任务。
蒋公对我宠信有加,不仅在我交通部长任内如此;我随 蒋公数十年,历任军政要职莫不如此,我实感受宠若惊。
感於 蒋公的知遇,崇敬 蒋公的人格,我唯有一心一意追随 蒋公、报效 蒋公,除此之外,数十年来我
在军、政各界,对事必尽忠尽职;对人则一无瓜葛。
我平生经历,可概括为以下数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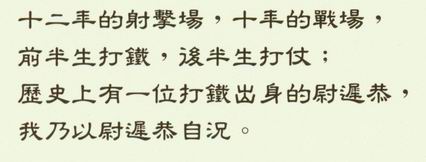
蒋公宠信我,并且近乎放任我,或许正是著眼於我这铁匠——但知“埋头打铁”。
兵器是铁做的。抗战初起,我接掌兵工署,督导全国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任期约十二年。
对日抗战,大小战役之不利,无日、无时、无地无之。可堪告慰者,战况再如何的不利,尚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 !
尤其日军攻陷南京以前,所有兵工厂被迫撤迁到西南大後方。打仗,前进非易,退亦极难,而我督导兵工厂西迁,是“有条不紊的退,全师而退”。
为了兵工厂的撤迁, 蒋公才破例到汉口,询问我有关事宜。在这以前和以後, 蒋公都不曾对我兵工署的工作有任何不满。
在汉口、南京、或在溪口,我与 蒋公的晤面寥寥可数,而这两三次在三个不同地方的晤面,先先後後所面临的处境,或者是来自日本军阀的,或者来自中共,率皆惊涛骇浪,势将翻天覆地,如大厦之将倾;存亡绝续,系於 蒋公一身。也就是在这样的非常之时、非常之地, 蒋公更显现其非常之人的不忧不惧,所以我由衷敬服。
每当风雨飘摇,危疑震撼之际,我都亲沐 蒋公从容不迫、慎谋能断、处变不惊的风范;那种“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不因时而异,不因地而异,不因人而异,不因事而异。
我这个“铁匠”,於总管全国兵器生产的同时,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器总教官;在射击场,我打枪给他们看,所谓“十二年射击场”便是指我这时候的工作环境。
政府迁台,民国四十三年,我接任国防部长。上任第一天,我只向本部官兵讲了五分钟的话,然後就由王叔铭等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陪同,搭乘洛阳舰,先到金门巡视一周,又到马祖,回台,再搭机到大陈。
就大陈全般形势分析研判,我向 蒋公报告:“大陈难守。”
国军由大陈转进,以使金马外岛防务更为坚强,这一战略部署影响深远,其成功端赖 蒋公英明决断。
敌我态势非常明显;自三十八年古宁头之战以後,中共对金马的觊觎无日无之,日甚一日。就我们而言,无金马则无台澎,保卫金马则保卫台澎。
我平生处世驾简驭繁,自定八字诀:“了解全局,把握要点。”
视察金马,建设金马,使固若金汤,是我担任国防部长的第一要务,也是我必须把握的“要点”。
我在金马的时间多,在台北办公室的时间少。至於台北的街道,我更是完全陌生。
说起办公室,我乐於藉此透露一段秘闻——
我的办公室与 蒋公的办公室原有一道门户相通。不论 蒋公来我办公室巡视,或是我到 蒋公办公室谒
见,都只须三、四个箭步而已,可是,十易寒暑,我既不曾踏入 蒋公办公室一步, 蒋公也不曾在我办公室出现一次。
当然,身兼三军最高统帅的 蒋公,何尝愿意看到一位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国防部长哩!
国防部长十年之中,一看再看,一访再访,金马外岛的一草一木,我如数家珍,相反的,任我独自闯荡陌生的台北街道,我即将旁徨迷惘,不知何去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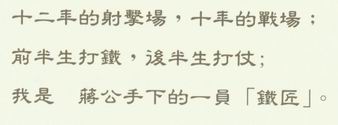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