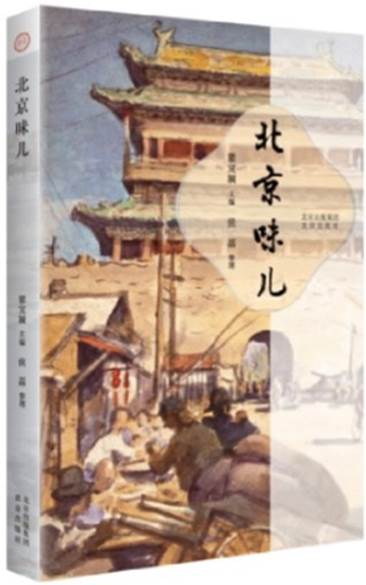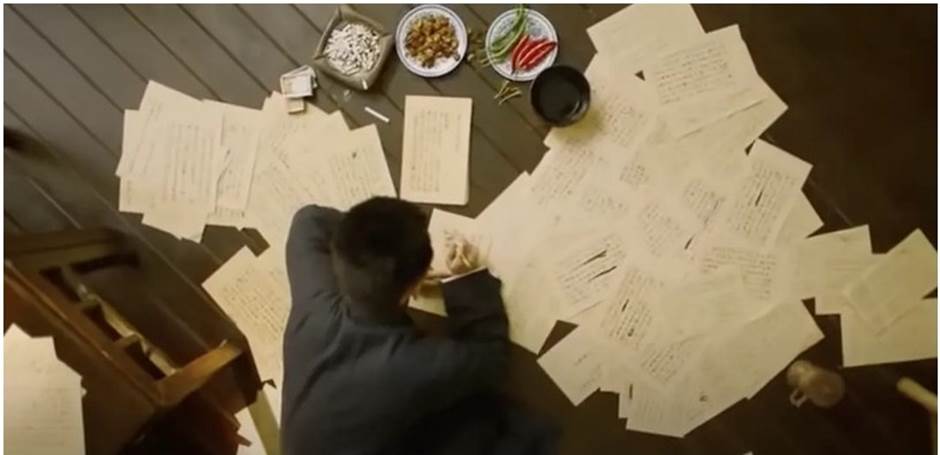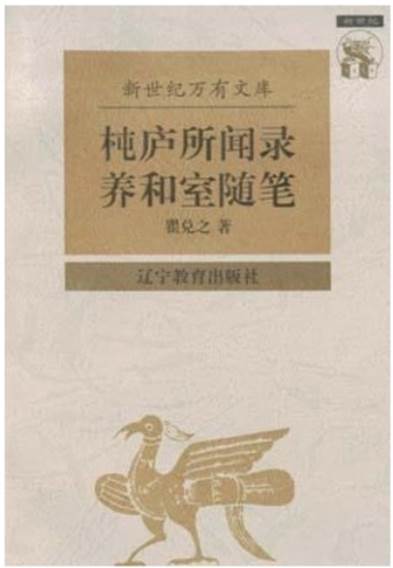|
瞿宣颖与北京:一位民国“史官”的居京日常丨京华物语 侯磊 “今天知道瞿宣颖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写下了大量文史和掌故学方面的著作。《北京味儿》一书,便是瞿宣颖关于北京历史人文、风物、掌故、教育乃至市井社会生活的文章。以下内容为侯磊对瞿宣颖的介绍,也是该书的“代后记”。
《北京味儿》,瞿宣颖 主编,侯磊
整理,北京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民国学者瞿宣颖(1894—1973)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在他八十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死于提篮桥狱中,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 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从文言、半文言写到白话;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他笔下跃然纸上的北京,可分为文言、白话两部分,编成两部大书。 北平史官 瞿宣颖早年在沪通过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学习,去京后辅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周刊》,并在其上发表了《文体说》《代议非易案书后》。自己开过广业书社,主编(总编)过《华北》月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和》月刊,名列众多杂志、丛书编委,众多诗社社宾,众多学术机构的发起人和工作主力,众多学会会员。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若干官职,而说他是“史官”,是因为他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参照各处的官制简章,现将职责简述如下: 国务院印铸局:“专职承造官用文书、票券、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刊刻政府公报、法令全书、官版书籍。” 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历史的一切材料。” 河北省通志馆:“向各地征集志料,编纂《河北省通志稿》,并要求各地编纂志书。” 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私人治学,为家存史。他在《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11月26日第七十二期,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资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可见他参考工作中的史料来治学,用私人治学来补官方之缺,并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可惜此处所指的那部“极翔实的新著”则无从问世了。 他认为:“吾国人于字画则知珍重,于史料则不甚顾惜,其毁于无知者之手盖不知若干矣。”而在《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中,他说:“我们所注意的不单是古代的历史,更要注意现代的历史,并且要准备未来的历史。” 何以是“未来的历史”呢?他在1945年所写有关《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顾》:“诚以人事靡常,零篇坠简,一旦澌灭,良可痛惜。得一刊物为之传载,即不啻多写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汉水,一置岘首,终有一传耳。”而与此观念不大相同的,是他的三代世交陈寅恪。陈寅恪始终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谈一点家事。 与此相符的,是瞿宣颖热心于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七七事变以后,北京古学院成立于北海的团城,于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担任院长、张燕卿担任副院长、瞿宣颖与吴廷燮、叶尔衡、田步蟾、周肇祥、王养怡、胡钧、郭则濂等为常务,所参与者皆为一时名士。学院创办了《古学丛刊》《课艺汇选》,仍旧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请人题写刊名。瞿宣颖从第1至5期,连续在其中的《文录》栏目发表文章,并且参与搜集了众多前人未刊的书稿,由郭则沄编印了《敬跻堂丛书》。
瞿宣颖
(1894~1973),别名益锴,字兑之,简署兑,号铢庵,晚号蜕厂、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任教。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精诗词书画,尤擅于文史掌故,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汉魏六朝赋选》《北平建置谈荟》《北平史表长编》《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方志考稿甲集》《长沙瞿氏丛刊》《补书堂讨录》等丰富著述。还著有《燕都览古诗话》,为咏览燕都之作,以诗系文,诗文并茂。其中有关什刹海地区的诗文有15篇。 他对官方的学术机构尽职尽责,且有着很强的期待。在《文化机关的责任》一文中写道:“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应该忘怀于一时的政治现象,而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说一句充类至尽的话:纵使国亡,而我们的事业却不可以中断。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 如果官方机构不够完备,他会加入别人组织的学社,如他参与由表兄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并编纂史料,所著《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纪略》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请他的母亲傅太夫人题写刊名,署名“婉漪”。就在参与古学院的同时,瞿宣颖在自己家中还成立一个学社——国学补修社,参与者除他自己,还有徐一士、谢国桢、柯昌泗、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等,聚会多是在瞿宣颖的半亩园。由大家轮番讲授国学知识,他把自己所讲的授课笔记整理为《修斋记学》,连载于《中和》月刊,并印成线装铅印本出版。 士大夫自由结社琴棋书画、交游论学的思路,是他家中世代的生活方式,他不会改变这种方式。 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 民国时热爱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颖的热爱远不止写几篇旧京梦华录,而是把职业前途都用在热爱上。鉴于北平历代方志都不够完备,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他想给北京做地方志。他在《国史与地方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固然要一部极好的国史,尤其先要有几部极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仅作为乡土教材培养人们热爱家乡的感情,更是国史的一部分,爱乡便是爱国。 而他与此相关的职位,是在天津担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主持编纂《河北通志稿》,并就编纂事宜与王重民、傅振伦等学者通信,也曾担任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负责上海通志馆的筹备。就私人治学上,他在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的天春园中饱览上千部方志,著有《方志考稿》《志例丛话》等。不论是风俗制度史还是方志学,都埋藏治掌故学的重要史料。这些,都是他为北平编纂史志的准备。 而具体工作,他是先后两次通过不同的学术机构,以及他在机构中担任的职位来实行的。 1929年9月,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个相当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机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干研究会,也有院士制度,叫作“会员”,一共有九十位。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地点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史学研究会有众多学术项目,首当其冲者是编纂《北平志》,为此还创办了《北平》杂志。 也许是学术带来的兴奋,瞿宣颖率先拿出了《北平志编纂通例》《北平志编纂要点》,列出《北平志》要分为六略:一、《疆理略》;二、《营建略》;三、《经政略》;四、《民物志》;五、《风俗略》;六《文献志》,算是定了个体例的初稿。又干脆自己编了本《北平史表长编》,都发表在《北平》杂志上。但这部《长编》限于写作条件,他并不满意,也曾受到过其他学者的议论,晚年时还对弟子俞汝捷谈起过,很遗憾没有再版修订的机会了。后来因为抗战,《北平志》的编纂工作被迫停止了。《北平》杂志只出版了两期。 另一次是到了40年代,由民国时清史馆总纂吴廷燮主持编纂《北京市志稿》。这部大书共有400万字,直至1998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一次瞿宣颖担任分纂,亲自编纂《北京市志稿》的《前事志》,“采用编年体,为上古至民国二十七年的北京大事记。”《前事志》原八卷,可惜如今仅存《清上》一卷了。 此时北洋政府的各大机构,官员工资并不低,公务相对清闲,不少人再兼几个闲差,或到大学里教书,有的月收入能达上千元。鲁迅、胡适等人都买得起房子,以保证学术和生活的体面。而街面上的警察或“骆驼祥子”月薪6元,租一套十几间房的三进四合院不过几十元,而全买下来需要近千元。此时的北平有古典的遗韵尚无现代化的破坏,有南方的秀丽且有北方的壮美,有皇城府邸的尊贵又有市井小民的窃喜;有廉价的饭食书籍尚无过多的机构冗员,有政府的高工资尚无政治的高压。瞿宣颖的生活,理应十分滋润。 然而,这位史官的居京生活是朴实的。父亲瞿鸿禨不大爱吃肉,多以素食为主,瞿宣颖也受此影响,并不是位老饕。他懂美食和生活品质,作有《北平历史上之酒楼广和居》《北京味儿》等文,不论是写涮羊肉还是谭家菜的鱼翅,皆得其中三昧(当然现在不该吃鱼翅了)。但他并没有过分追求,只是从小生活水平较高。他笔下的北平,是“面食与蔬菜随处可买,几个铜子的烧饼、小米稀饭、一小碟酱萝卜,既适口又卫生。……蓝布大褂上街,是绝不至于遭白眼的”。至于梨园鼓吹、斗鸡走狗、声色犬马,则没什么兴趣。他写过篇《记城南》,但他不热衷于逛天桥看打把式卖艺。诚然,平民娱乐也绝非低人一等,能如王世襄写架鹰、唐鲁孙写美食、张次溪写梨园、连阔如写江湖买卖道儿上“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的人更为金贵。瞿宣颖并非不懂这些,也偶尔会谈及一点,但学术兴趣并不在此。这一点上他很像周作人,仅以故纸堆自娱。 因此瞿宣颖的掌故不集中在吃喝玩乐、风土人情上,而是将历史事件、历代典章信手拈来,本质上是在写政治制度和风俗制度;更本质上,则是他史学研究和编方志的副产品。今人的“豆腐块”味道不如前人,是因为只有副产品,而缺少治学的主干。 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 尽管瞿宣颖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如他住过北池子、住过东四前拐棒胡同17号,1924年其时寓所已迁黄瓦门织染局6号,在京郊住过香山碧云寺,而他住得最久的地方始终是位于弓弦胡同内的牛排子胡同1号的半亩园东路,前后共四进院落,现在属黄米胡同。 这所不小的宅院原先是《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江南河道总督完颜麟庆(1791—1846)的故居,东部为住宅,西部为花园,瞿家只占东部,是瞿鸿禨时代置办下的。瞿宣颖读书求学,并生儿育女,直至儿子在这里结婚,孙子在这里出生,并最终与妻子离婚,并单人于1946年赴上海(家人在1948年去上海),后陆续将半亩园东路卖出。他写过《故园志》,请齐白石画《超览楼禊集图》。长沙故宅中有两株海棠,而黄米胡同宅中仍有两株海棠,他请黄宾虹绘《后双海棠阁图》,并请郭则沄、黄懋谦、傅增湘、夏孙桐等《为兑之题双海棠阁图卷》题诗。 他是《人间世》《宇宙风》杂志的作者,《旅行杂志》《申报》月刊、《申报·每周增刊》也是他的发稿阵地,对于北平,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且把一切赞美之词留给了北平。他写道:“我是沉迷而笃恋故都的一人。”“舒适的天然环境,实是最值得留恋的。”“要找任何一类的朋友都可以找得着的。”“北平有的是房屋与地皮,所以住最不成问题。……生活从容,神恬气静……”他认为北平如果以公元938年辽太宗定幽州为南京,到1938年已经是建都一千年了。作为千年故都,北平必应当隆重庆祝,大书特书,且需要整理的学术遗产太多了。 《宇宙风》在1936年第19、20、21期,出过三期《北平特辑》,每辑都是名篇辈出。第19期前四篇文章为: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坏》(署名:知堂)、老舍的《想北平》、废名的《北平通信》、瞿宣颖的《北游录话》(署名:铢庵)。《北游录话》采用铢庵(作者自己)、春痕(挚友刘麟生)二人对话体的形式,分成十章连载十期,写铢庵带着春痕游览并谈论北京。而第十章《北平的命运》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表达出瞿宣颖对抗战前北平命运的担忧。在他心中,北平不只是文化古城,更是近代学术的中心,自古以来有着士大夫自由讲学的传统。而面对日本的侵略,“以此为中国复兴之征兆,亦未可知啊!”这三期特辑的文章被陶亢德编成一本《北平一顾》出版。也许是《北游录话》太长,并未收录。 瞿宣颖喜欢实地考察和旅行,他热爱地方风物,每到一处都要走访文物古迹,恨不得立刻研究当地风土。他为张次溪《双肇楼丛书序》作序称,张次溪研究北京能“亲历闾巷,访求旧闻”,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写有《燕都览古诗话》,每一处景观作一首旧体诗,并引用旧京古籍讲解论述。京城的中山公园、什刹海是他与友人游览、品茶的地方。故宫、皇城还是各皇家建筑,他都曾亲赴考察,并感慨大量清宫中没有算作文物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已残破丢失(这在当时人眼中不算文物)。他赞同朱启钤修改北京的前门楼子,认为这是成功的、现代化的修缮。而到1924年前后,市政公所几乎拆光了北京原有13公里的皇城城墙,他对此大为遗憾。皇城城墙今天只剩下1900米了。
《燕都览古诗话》,瞿兑之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京郊各个旅行胜地,昌平的汤山镇、延庆八达岭、房山的上方山、京西的三山五园,直至潭柘寺……都留下他的足迹,写有旧体诗或游记文章。至于京外,他游览定县,做《古中山记》;赴广东执教于学海书院,做《粤行十札》;游览大同,做《大同云冈石窟志略》。他希望南开大学设立一个机构,用以搜集天津地方史料,为将来做《天津志》做准备。而那些旅行之地,成了他考据的现场。 任何一个地方,要接续上它的历史,就要掌握此地历代先贤的著作。瞿宣颖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故宫遗录》等,辑录、整理、出版了不少。他根据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等,辑录出《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撰写了《北京建置谈荟》《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等长文,编辑出版了《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辑:共有《京师偶记》(柴桑)、《燕京杂记》(佚名)、《日下尊闻录》(佚名)、《藤阴杂记》(戴璐)、《北京建置谈荟》五部书。前四部是清人所著,而第五本是他自撰。这套书他请史学家陈垣作序,并由梁启超来题签。他在致陈垣的书信中说:“《北京建置谈荟》,则颖所自撰也,书虽不足观,以供普通人浏览,稍稍传播爱护史迹之观念,未为不可用也。”(《陈垣往来书信集》兑之致陈垣书第二通)由广业书社出过石印、线装铅印两版,这个书社还出版了一套《明清珍本小说集》,以及瞿宣颖编著的《时代文录》上下两册,《汉代风俗制度史》等。广业书社位于牛排子胡同1号,就是瞿宣颖的家——他自己办的出版社。 他写了大量的旧京掌故结集为《故都闻见录》《北梦录》等。掌故既是文章的内容,又是一种近似于古代笔记的、半文半白文体。他研究旧京有自己的体系,想建立现代化的掌故学。而这种文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日趋白话。晚年时,他在上海以瞿蜕园为笔名,给《新民晚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写了不少旧京掌故的白话文,能读出他是用文言思考,再落笔为白话的。那些豆腐块他往往一蹴而就,一刻钟写完,至今读来妙趣横生。 始终是旧体文学活动的组织者 文人几乎是一半写一半社交。瞿宣颖朋友极多,且他的社交也能分成几拨人。 一拨人,是他先天的亲友。瞿家与逊清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同僚、姻亲关系,后裔们时常走动。也包括他幼年时师从王闿运、王先谦,少年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青年时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的同学。这拨人更多的是结社雅集,诗词唱和。传统诗社多是以家族、姻亲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与连襟张其锽、卓定谋,表兄朱启钤,湘学同门齐白石,译学馆时的好友黄濬,圣约翰大学时的好友刘麟生、方孝岳、蔡正华,以及旧名士溥心畬、李释戡、夏仁虎、冒鹤亭、傅增湘、章士钊、郭则沄、罗惇、黄懋谦、夏孙桐等。 另一拨人,是不左不右、偏于中庸的文史作家。如《宇宙风》《古今》《逸经》《越风》《天地》《新民》《文史》《杂志》……包括《古今》主办人朱朴、《逸经》主编谢兴尧、《文史》主编金性尧……以及各自的作者群。这里除了周作人,几乎都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在《周作人日记》中,曾有多次写瞿宣颖前来拜访。他为周作人的代表作《日本之再认识》,写过一篇《读〈日本之再认识〉》的评论,并为其《名人书简钞存》写了数百字的按语。 仔细想来,这两拨人多有交集,本质上是知识结构和趣味点近似的同一拨人,更像年龄断层的两边。旧名士们的辈分更长,文章更偏于文言。他们都成为瞿宣颖主编的《中和》月刊的作者。 《中和》月刊被瞿宣颖恢复成杂志的本意:“杂的志”。杂志没有编辑部成员名单,卷首语、编者按都署“编者、编辑部”,很多都是瞿宣颖亲自写的。凡是发现了未刊的名家手札、史料整理、新颖史论会立刻刊登,形成周作人、钱稻孙、徐一士、孙海波、柯昌泗、谢国桢、谢兴尧、傅芸子、傅增湘、俞陛云、周黎庵、金性尧、陈慎言、孙作云、张次溪等掌故、民俗学家的混合阵营。一时间,郭则沄在此连载《庚子诗鉴》《红楼真梦》,徐一士连载《近代笔记过眼录》,蒋尊祎连载《天治》;瞿宣颖自己连载《养和室随笔》《燕都览古诗话》《方志余记》,更连载先贤未刊著作如王闿运《湘绮楼集外文》、瞿元灿《公余琐记》、耆龄《赐砚斋日记》等。此前,他主持国立华北编译馆,日常还招集华北编译馆的干事、课长开会商议各项事宜,办公地址在北海公园内的清净斋,并负责主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
《中和月刊(全十二册)》,《中和月刊》社 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旧式的家庭关系是紧密的,瞿宣颖与亲友走动频繁。他对待亲友,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叫“序而刊之”(或“跋而刊之”):把对方的未刊著作找来整理,作序、题跋、题词、题签、编校……直至印刷。他在《中和》月刊上开辟《超览楼藏耆贤书札》栏目,将家中所藏的郭嵩焘、俞樾书札等刊登出来。共同出身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名诗人黄濬被处决后,瞿宣颖将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从杂志上搜集起来,编纂成单行本并作序刊印。此版的纸张奇缺,仅印一百部,为藏书界珍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为徐一士、张次溪、高伯雨、刘麟生等写过序;编校汪诒年纂辑的《汪穰卿先生传记》、燕谷老人《续孽海花》、连襟张其锽的《墨经通解》和《独志堂丛稿》,与表兄朱启钤共校姨父黄国瑾的《训真书屋遗稿》、校《贵州碑传集》等;为陈宗蕃《燕都从考》、张次溪《双肇楼丛书》、蔡正华《元剧联套述例》等题词;至于题写书名、刊名或自署更是平常。他对个人著作,几乎都作自序或编序例,并请人题签。历史的载体是文献和文物,文献最重要的是刊印。旧文人的风气是他的生活日常,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留住历史。 他与画家黄宾虹、齐白石相交甚好,另与陈衡恪、于非闇、陈半丁等相熟。他写了《宾虹论画》《齐白石翁画语录》等文,以记录与黄宾虹、齐白石谈画的金句,使得当时的只言片语,成为后学中珍贵的圭臬。1943年,年近七旬的张鸣岐来到北京。张鸣岐(1875—1945)即张韩斋,清末时的两广总督,为广西的现代化做了不少实事。此时做过总督的人在世者只有他和陈夔龙了。瞿宣颖来听他谈前清旧事,并随问随记,作《记所闻于张韩斋者》,晚年又修改为《记张韩斋督部语》一文,收入《补书堂文录》。两年后张鸣岐就逝世了。 早在1931年在沪时,瞿宣颖便为丈母娘曾纪芬笔录了《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为丈母娘的父亲曾国藩写了本《曾文正公传略》和若干文章,为老丈人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的公牍出版题跋……亲戚中的重要历史人物,都被他捋了一遍(他这样的人在古代叫“肉谱”)。就北洋政府的往事,他也写过《黎元洪复任总统记》《北洋政府内阁人物片段》等;就个人经历,有《故宅志》《塾中记》《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等。当时没有口述史的概念,但瞿宣颖有做口述史的意识。口述史的整理者要在史学上不逊于口述者,能将口述梳理成文并校订正误,很见功力。 北平竟然集中了那么多的“文化遗老”,他们支撑起五四运动以来旧文学的半壁江山。瞿宣颖始终是旧体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正如他在五四时的《文体说》一文所讲:“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用于文言。”他知新而不忘旧,继续让传统文学在其自己的轨道上前行至今。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存史之心 太史公有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而到了民国,瞿宣颖作掌故学,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为了“存史”。 瞿宣颖生于清末,成就于民国。他所面对的改朝换代,结束的不是有清一代,而是两千年来所有的帝王,是整个古代的生活细节。中国从此没皇上了,那么有皇上时的一切都没用了。没用之物,首选是抛进垃圾堆,而不是送进博物馆。民国人不把晚清的东西当文物,越是当时的学者,越认为不值得进博物馆。经亨颐曾认为要把故宫卖掉,清宫秘档也变成八千麻袋的废纸出售,激进者多有废中医、废汉字、废旧戏的言论。改朝换代便是旧臣败家,新暴发户闪亮登场,京城八旗阶层败落,众多王公生活无以为继,哪顾得着存旧物?这便意味着历史中断。更何况瞿宣颖笔下那些“杂史”——历史的边角料呢? 而瞿宣颖自幼家中来往,无不是逊清重臣;他所求学、交往的无不是宿儒;家中翻检出前人的旧纸,无不是郭嵩焘、康有为、岑春煊等一辈名士之间的通信手札。他的掌故学有一半是天生而来的:自家和亲友即为半部近代史,任何旧事旧识都是写掌故的素材。他有意识甚至是下意识地保存家族、亲友和个人的史料,好像是一位每天都为孩子拍照的父亲,也像任何东西都要搜集的收藏者。四十岁时,瞿宣颖因兄丧,从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和河北省通志馆馆长的职位上辞职返京,客观上给了他编校先人著作的时间。为了恪守母亲傅太夫人的遗命,他整理并刊印了线装铅印本的《长沙瞿氏丛刊》二十卷,包括瞿氏三代的文稿、家谱,特别是父亲瞿鸿禨的《超览楼诗稿》等,因为“苟不汇集刊行,实惟散失之惧”,“家谱与方志,皆为国史之根源”。编国史所练就的功力,首先要用在编家史上。 纵观他一生工作的“标准流程”,始终是:成立学术组织——搜集整理史料——研究并讲学著述——编校前人著述——序而刊之。就像旧时文人造园,请人将园林画成长卷,雅集时每人于长卷后题词作诗,自己再作总序,把诗文绘画,付之桑梓。众人吹拉弹唱,尽欢而散。多年后江山易主,园林荒废,老友凋零,此时展卷重读,借着夕阳念旧时春光。
《杶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瞿兑之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因为时局的变化,他不得不于1946年离开北京寓居上海,并独居卖文为生。而最终在“文革”中被抄家,瞿家世代的收藏连同他大量的文稿散失殆尽。他本人75岁时入狱,并在80岁时死于狱中。这五年他除了一些自述和交代材料以外无法治学写作。然而,他毕竟留下了大多数的著作,留下了瞿氏家史、北京史志及自身带来的掌故。即便在不能出版时,他仍整理好了平生的《补书堂诗录》《补书堂文录》,并影印、油印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一个人几乎干了三个人,甚至十个人的活儿。如今瞿宣颖仍有大量未刊手稿、书信藏于各大图书馆或民间藏家手中,时常出现在拍卖会上。更有大量秘辛从未写过或讲过,被他带走了。 他的先知之举还有:在抗战前把瞿家残存的古籍1811种共59769卷运到北平,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馆编印了《瞿氏补书堂寄存藏书目录》,连双方交涉的通信和律师证明一并印上。书是永久的“寄存”了,但长沙故宅是彻底在战乱中毁掉了,“寄存”总比毁掉要好。 每个家族,每位名士都成于时代,兴于时代,最终湮灭于时代。长沙“善化相国”一家,从瞿鸿禨到瞿宣颖,在官职、财产、家传文物、藏书方面都“代降一等”,直至被抄家后损失殆尽——这是推翻旧文化,打造新文化的必然;但在诗文学术上并未下降,直至瞿宣颖的侄子瞿同祖(1910—2008),又是一代大家。同样,尽管历经破坏和拆迁的风险,杭州永福寺畔的瞿鸿禨墓总算保住了。世事变迁没能给瞿家人留下家传的藏书、文物和财产,但留下了前辈著作、家谱、子孙和祖坟——在物的层面没保住,但人和精神的层面保住了,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本文选自《北京味儿》,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文/侯磊 摘编/安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陈荻雁 |